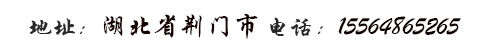人皆言佛系,我却向人间草木借三分真性
|
去岁男神女神纷纷, 今朝佛系群众处处。 倘若云门见着,一并打杀与狗子吃去。 一首打油诗,权当是开场白、“定场诗”。一夜之间,社交媒体上“佛系”一词横行,仿佛只要日子过得寡淡、对人对事无动于衷,便是自带“佛系”标签了。 也听人说,石菖蒲是很“佛系”的。说来好像也对,石菖蒲自古以来为文人高士引以为伴,多少就沾点仙气、禅意;它又“不假日色”,一幅与世无争的样子,何况“不资寸土”,更似无欲无求。 今日午后菖蒲即景 但是如果说到石菖蒲,就只能反反复复在这几句话里打转(坦率地讲,现今很多讲菖蒲的文章基本都这样),那便是给自己下套。英语里的tautology,直译过来倒是形象——“套套主义”,无非是给自己设定一个接一个条条框框,与贴一个“佛系”标签没什么两样。 “佛系”本身没什么不好,然而千篇一律的“佛系”却糟糕得很。 正如一株石菖蒲,你摆在茶席上便是雅,放在墙脚则是朴,丢在养鱼的水槽里还能净化水质,可以形而上,也可以实实在在践行功能主义。但如果你强求一个标签,非要去规定个“佛性”如何如何,那么必然是南辕北辙,更不要提“拈花微笑”了。 午后案头即景:狼尾蕨与火山石 于是我想,在“拈花微笑、不立文字”之前,不若先跳出束缚我们思维的窠臼,于我们熟知的人间草木中,借一些别样的性情,你掺三分,他借一半,是不是便不是千人一面的“佛系”了呢? 朴素中的顽强——苏东坡 草木是有性子的,且性子朴素得很,什么玄虚都不玩。野外采回来的石菖蒲,根须都扯断了还能继续发芽发根,那是因为茎里面存储着充分的备用养分。种在家里面的石菖蒲经过修剪会越来越纤细,那是因为它要适应养分稀少的生长环境。 莫要说它无欲无求。你试试看给它宽广肥沃的水土滋润,一样能重又发得野性十足,活泼泼,大喇喇。 一切都没有什么玄乎的,只不过是要随遇而安,适时而动。这便是草木教给我的道理,是朴素里透着顽强的性子。 相依:白马纹石与雁荡山野菖蒲 同样朴素而野性的石菖蒲,在北宋年间,曾让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,在陕西关中平原的凤翔地方,为它们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菖蒲诗: 自我来关辅,南山得再游。 山中亦何有,草木媚深幽。 菖蒲人不识,生此乱石沟。 山高霜雪苦,苗叶不得抽。 下有千岁根,蹙缩如蟠虯。 长为鬼神守,德薄安敢偷。 霜雪虽苦,石菖蒲却经年累月,将根紧紧扎进大地。即便叶子为寒冬所镇压,那又如何?如蟠龙一般有力的错节老根,又何尝不是生命力的象征? 这位年轻诗人,名叫苏轼。也就是在这段居于凤翔的岁月里,苏轼留下了或许是他在后世最有名的诗句之一: 人生到处知何似,应如飞鸿踏雪泥。 泥上偶然留趾爪,鸿飞那复计东西。 穷困里的创造——沈三白 看见有人说,今日之“佛系”,多多少少不过是前阵子“丧文化”的变种。这话是有道理的。 在别人眼里,沈三白大概算得上一个比较“丧”的人。虽然有学识文化,却不参加科举。家道中落以后,却也没有起过复兴家园的志向。看他的一生,或者卖画,或者为人家作幕僚,不管哪个行当,都赚不了钱,还常有被裁员、喝西北风的危险。 然而这样一个人,只要遇到自己有兴趣的事情,就变得生气勃勃起来。比如“幼时闲情”一节中,看到夏天里聚集在一起飞的蚊子,他能想象成“群鹤舞空”,甚至还将蚊子放到帐中,以烟徐徐喷之,制造出鹤舞云霞一般的场景来。 附石虎须与竹叶石斛影,借沈三白神思之妙,取寒鸦栖树、蒲草冷汀之意 沈复的许多“创意”,都是与穷有关的。但是这个人真的妙得很,种水仙却没有灵璧石相配的时候,他能想到用煤炭中“有石意者”来代替;买不起宣石造假山,他能想办法用山里捡来的黄石搭一个小型山水盆景。 而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中所说的播种石菖蒲籽的做法,他也依法实践,娓娓道来: 《浮生六记》 “如石菖蒲结子,用冷米汤同嚼喷炭上,置阴湿地,能长细菖蒲,随意移养盆碗中,茸茸可爱。” 或许,“可爱”的,还有爱妻芸娘咀嚼石菖蒲籽与掩嘴喷吐的有趣模样吧。我妄自揣测,就中妙处,恐不足为外人道也,抑或沈三白只为独享,故未在《浮生六记》中细细展开了。 但我深信,像他这样的妙人,一定会享受到这样的妙趣的。 我也时常想,沈复与其爱妻芸娘的这些许“创意”,换了旁人处在他们的视角中,是否会享受到同样的乐趣。我猜恐怕是不会的。这并非是审美高下之别,而只是“自我”与“他人”的区别而已。 所谓自得其乐,最终的落脚点,不在于“乐”,而是一个“自”字。 闲情外的决绝——文震亨 既然都已经提到文震亨了,不妨再为他也写上两句。文震亨若活在当下,大概会被视为“佛系”作家的一员吧——出不出名随缘,出不出版随缘,赚不赚钱随缘。 虽然身世显赫,文氏家族更是当时江南文化界翘楚,文震亨却只是一章一章地写他的《长物志》,好将这些有关“多余之物”的知识,还有那一代人的闲情逸致传递下去,不致失了踪迹。 负喧之乐:文竹影与旧书箱 “弄花一岁,看花十日”,这是《长物志》中“花木”一节的开篇,又何尝不是文震亨写给后来者看的作者心迹呢? 今天我们这些“玩物忘忧”的人们,多多少少,都是受了文震亨的恩惠的。 但就是这样一个与世无争也无求的闲散人,当朝廷倒行逆施残害忠良时,他是那个站在苏州街头领头抗击之人;当满族统治者发布剃发令时,他是那个自沉于河的决绝之人。 刚养菖蒲的时候,什么品种都想收集一些,然而金钱菖蒲始终养不好。大约是身在城市高楼的关系,通风湿度都难以达到。有时候也会抱怨金钱菖蒲太娇气,然而其实矫情的,终归是我自己。若无法适应,菖蒲就变得刚烈得很,无论你自以为倾注了多少爱心,它都自绝给你看。所以我现在养着能适应家中气候的品种,也乐于欣赏别人家啊“迎娶”回去养得好的金钱。只是自己不再做非分之想。 如此相忘于江湖,也是很好的。 午后即景:虎须与酢酱草 既然我们说到了决绝,那就绕回开篇的定场诗吧。 在那首歪诗里,我说到“倘若云门得见”,自然是引用云门文偃禅师说如果给他见到唱偈“天上地下、唯我独尊”的刚出世的佛祖,就要“一棒打杀与狗子吃”的典故。禅门公案难懂,不过粗浅大意还是解得的,无非是说,莫要被条条框框——管它是偶像、教义、命令、主张还是标签——束缚了头脑。 千利休辞世句里说,吾这宝剑,祖佛共杀。也是一样的决绝。 打杀了才好。打杀的是标签,是拘束,是刻板印象。倘若真有“佛性”这样东西,大概唯有靠这“祖佛共杀”的宝剑,才能激出每个人自身具有的“性情”。 所以卡尔维诺才说,希腊神话里,英雄珀修斯杀了美杜莎,能将人化为沉重石像的女妖流出的鲜血里,方可诞生轻盈翔天的飞马。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shichangpua.com/scpgx/1397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耳聋患者或朋友快收藏吧,改善生活的食疗与
- 下一篇文章: 冬季进补吃羊肉,哪些人不适合